華為股權結構解析
2024-09-11 16:58:47 來源:互聯網轉載或整理一年一度的“華為分紅”又上演了!近日,華為宣布:2020年度華為持續股權分紅,預計每股1.86元。根據華為約10萬員工持股,分紅總股本約220億股計算,本次分紅總額將達到400億元,人均分紅
一年一度的“華為分紅”又上演了!近日,華為宣布:2020年度華為持續股權分紅,預計每股1.86元。根據華為約10萬員工持股,分紅總股本約220億股計算,本次分紅總額將達到400億元,人均分紅40萬元。
相比2019年度每股分紅2.11元,華為2020年度分紅數額絕對值上略有下降,但在疫情和外國持續打壓下,能取得如此分紅業績,已實屬不易。且華為在面臨巨大生存困難情況下,依舊堅持分紅,把錢分給員工,更難能可貴。
筆者在辦理公司股權架構設計與員工股權激勵的實踐中,經常遇到客戶說要做一個和華為一樣的股權架構,或者是做一個和華為一樣的員工持股。
在這個公眾號,筆者曾簡單寫了一篇《從法律的角度看華為的“虛擬受限股”》的短文,主要是介紹華為員工持股的持股工具——“虛擬受限股”的法律性質。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華為公司的股權架構設計,看看能帶給我們什么啟發?
華為的主體運營企業為: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簡稱“華為有限”),其只有一個股東: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簡稱“華為控股”)。
華為控股有兩個股東,即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簡稱“華為工會”,持股99.1235%)和自然人任正非(持股0.8765%)。
華為的股權架構如下:
問題一:華為工會、任正非為何不直接持股華為有限,而是持股華為控股,然后通過華為控股間接持有華為有限的股權?
一個原因是:設置一道“防火墻”。華為的員工股東如就股權問題產生糾紛,只能是在華為控股層面,而不會影響到經營實體華為有限。
經常會看到民營企業的股東之間鬧矛盾,動輒申請法院凍結企業賬戶或企業資產,或是對企業使用股東知情權進行查賬,等等。這些,難免都會影響實體企業的正常經營。
所以,在實體企業和出資股東之間設置一道“防火墻”,即建立一個持股平臺,讓股東之間的紛爭只在持股平臺糾纏,而不會燒到實體企業,就不會影響實體企業的日常經營。
采用此“防火墻”設置股權架構的優質企業,再舉一例:
淘寶網的運營實體: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簡稱“淘寶公司”),其只有一個股東:杭州臻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臻希投資”)。臻希投資的股東為兩個,即杭州臻強投資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簡稱“臻強合伙”,持股50%)與杭州臻晟投資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簡稱“臻晟合伙,持股50%”)。這兩個有限合伙,均為管理層持股平臺,出資人為張勇等五位自然人(均為阿里巴巴管理層成員)。
淘寶網的股權架構如下:
第二個原因:員工股權承擔分紅稅負是一樣的。如華為工會、任正非直接持股華為有限,華為有限向股東分紅時,任正非承擔20%的“股息、紅利所得”個人所得稅;其它持股員工通過華為工會亦承擔20%的“股息、紅利所得”個人所得稅。
現在華為工會、任正非通過華為控股間接持股華為有限。華為有限向華為控股分紅時,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所得為免稅收入。故華為控股收到的華為有限的分紅是不交稅的。
華為控股再向股東任正非、華為工會分紅時,任正非和其它持股員工(通過華為工會)仍繳納20%的“股息、紅利所得”個人所得稅。
因此,無論直接持股還是間接持股,包括任正非在內的持股員工對于分紅所得都是20%的稅費負擔。
既然分紅的稅負一樣,間接持股還能取得“防火墻”作用,當然選擇間接持股模式。
問題二:華為控股的股東為何要兩個,任正非僅有的0.8765%股權為何不也放入華為工會?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回答:華為控股的股東可以是工會一個股東嗎?或者說,工會可以單獨設立一個全資子公司嗎?
《公司法》第57條規定,一個自然人股東或者一個法人股東可以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根據這個規定,非法人的單位或組織就不能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比如,有限合伙企業,其不是法人組織,故一個有限合伙不能單獨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
所以前面所述的淘寶公司穿透后的實際股東,是張勇在內的五個自然人,但鑒于一家有限合伙企業不能單獨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故他們五個人設立了兩個一摸一樣的有限合伙,才成立了“防火墻”公司——臻希投資。再由臻希投資單獨設立具體運營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淘寶公司。
那么,工會是法人組織嗎?
回答是肯定的。工會是在民政部門登記成立的社團法人,是法人股東,可以單獨出資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例如:南京銀行工會委員會單獨出資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南京銀資物業經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既然工會可以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為何華為控股的股東是兩個,在工會之外,再列一個任正非?
筆者冒昧揣測,原因在于給予任正非的“一票否決權”。根據公開的報道,華為公司的公司章程里給了任正非在重大事項上的“一票否決權”(但據任正非所說,他從來沒有用過這個一票否決權)。
根據《公司法》,股東之間可以就股東會上的表決機制進行特別約定,股東之間可以約定某個股東對若干事項的決策擁有“一票否決權”(事實上,現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也賦予國有股東在混改企業重大事項決策上的“一票否決權”)。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任正非要擁有對公司重大事項的一票否決權,得有個前提:任正非是這個公司的股東。
如果任正非還是放在華為工會里,華為公司就不能依據《公司法》給予任正非屬于公司股東的“一票否決權”。所以,任正非得是華為公司的直接股東。
根據公開報道,華為已考慮“后任正非時代”的“一票否決權”的傳承:“華為會從退出歷史舞臺的董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和高級領導中,選舉7個人組成一個核心精英團隊來行使否決權。”
所以,今后“一票否決權”的行使主體,將不再是“任正非”個人,而是給予“7人精英團隊”。這個團隊會成立一個可以擔任公司股東的組織,來代替任正非成為華為公司的直接股東,從而享有到“一票否決權”。
這個組織的組織形式,我判斷不會是有限合伙形式,應該是有限公司形式(考慮稅負和表決機制),我們拭目以待。
問題三:為何選用工會作為員工持股的代持組織,而不用其它組織形式?
員工作為自然人,其投資入股公司,有以下三類形式:
1、作為自然人股東直接持股。
這個想法很美好,但現實很殘酷,只能說你“想的美”。看看那些“有名”企業,能成為自然人股東的“非富即貴”。要么是有錢的個人投資者(比如“天使投資人”),要么是公司實際控制人或其直系近親屬(父母、配偶、子女,等等)。
一家公司的自然人股東太多,會有諸多不便,這里不贅述。就華為而言,間接持股員工達到10萬人,也顯然遠遠超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50人的人數限制。華為又不準備上市,持股員工想成為直接持股的股東,顯然是不可能的。
2、通過持股平臺間接持股。
員工持股平臺又可以分為兩類:
(1)實體型(即持有相關證照的)
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型、有限責任公司型、有限合伙企業型、員工持股會型(在民政部門登記,有社團法人證書,但2000年后逐漸取消,現已沒有)。
持股員工為這些實體組織的出資人。但這些實體組織,法律上也有對股東人數的限制,所以多于華為來說,不適用。
(2)契約型(即合同關系)
包括契約型私募基金、信托計劃、資產管理計劃(簡稱“三類股東”)。持股員工與前述基金管理人、信托受托人、資管管理人前述委托合同,投資入股公司。
如主體公司是上市公司或新三板掛牌公司,前述“三類股東”在中證登那邊可以直接登記為股東。但如主體公司是非上市、非掛牌企業,工商局不會把“三類股東”直接作股東登記,往往用管理人或受托人代為股東登記。
“三類股東”有管理費、托管費的相關支出,且在出資人人數上也有限制(不超過200人),而且往往有存續期(一般不超過7年)。故對于非上市、非掛牌的華為來說,顯然也不適用。
3、委托代持
持股員工委托某個人或組織代持。
除某些特殊情況,一般情況下,股權代持是法律所允許的。代持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業(如有限公司或有限合伙),或其它能夠作為股東的組織。
華為的工會持股,法律本質上是一種代持。但不是持股員工個人與工會之間簽署代持協議,而是持股員工組成的持有人代表大會選舉出的理事會與工會簽署代持協議。
因此,華為工會本質上不是華為員工的持股平臺,因為華為工會的出資人不是持股員工。華為工會其實是代持人,只不過是理事會與華為工會簽署代持協議。這種現象,在2000年至2006年國企改制中,頗為常見。在還允許員工持股會取得社團法人資質的時候,員工持股會作為持股平臺成為主體公司的直接股東。在員工持股會不能取得社團法人資質,即不能工商登記為股東的時候,就由虛擬的員工持股會下設的理事會與企業工會簽署代持協議,代為工商登記。
華為員工持股的代持人不選擇某個個人,或某個企業,筆者判斷原因在于不論個人代持,還是企業代持,均存在不可控的風險(比如個人債務糾紛、死亡風險、離婚分割風險,代持企業的出資人風險等),而用工會代持,能夠排除前述風險,而且工會不代表私人,具有公信力。
說到這里,大家看懂華為公司的股權架構設計了嗎?可以給我們的啟發是:誰來做股東?如何做股東?
- 上一篇:內部收益率計算公式詳解
- 下一篇:現在做什么最賺錢比較快的
其他文章
熱門文章
-
 打工老板的結局
2023-10-24
打工老板的結局
2023-10-24
-
 洪漢義12個明星女友名單(14K洪漢義回
2023-09-11
洪漢義12個明星女友名單(14K洪漢義回
2023-09-11
-
 洪漢義12個老婆名單(真正的14k老大女
2023-07-31
洪漢義12個老婆名單(真正的14k老大女
2023-07-31
-
 723甬溫高鐵為什么埋車廂
2023-10-25
723甬溫高鐵為什么埋車廂
2023-10-25
-
 上海70歲以上老人存款規定 上海老年人存
2023-11-19
上海70歲以上老人存款規定 上海老年人存
2023-11-19
-
 瘋癲辦公室人物介紹
2023-10-20
瘋癲辦公室人物介紹
2023-10-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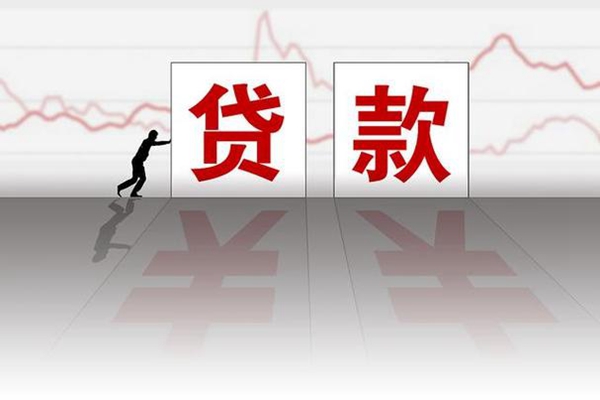 成功開導老婆接受別的男人案例(男人如何洗
2023-09-03
成功開導老婆接受別的男人案例(男人如何洗
2023-09-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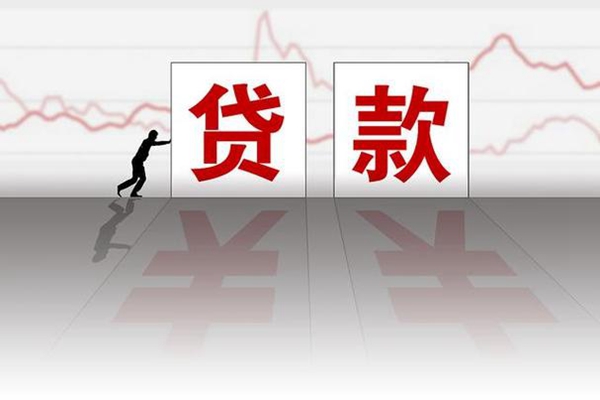 九一制片廠潘甜甜個人資料(紅人潘甜甜落網
2023-09-17
九一制片廠潘甜甜個人資料(紅人潘甜甜落網
2023-09-17
-
 大耳朵圖圖毀童年牛爺爺和圖圖媽(哪里能看
2023-09-11
大耳朵圖圖毀童年牛爺爺和圖圖媽(哪里能看
2023-09-11
-
 山東最不易發生地震的市
2023-10-18
山東最不易發生地震的市
2023-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