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辯論代表人物(以詭辯著稱的名家從何而來又為何沒落)
2023-09-25 01:29:55 來源:互聯網轉載或整理但凡提及中國古代著名的辯題,自然少不了“白馬非馬”這一命題的存在,而白馬非馬的典故,則又和諸子百家中一向以詭辯著稱的名家有著莫大的淵源。
從現有的史料文獻上來看,白馬非馬的命題最早出現于名家代表人物公孫龍子的口中,并被收錄于《公孫龍子》一書中,為世人揭開了一種不同于正常辯論的形式,即我們所俗稱的詭辯派。
何為詭辯呢?說白了就是有點兒讓人摸不著頭腦,很容易就被對方在言語中繞進邏輯的怪圈。
就以白馬非馬為例,當年公孫龍子出城的時候,遇到了城卒的阻攔,因為按照君侯的規定,城門不允許馬匹的進出。但公孫龍子卻言馬也白馬并非一種物體,因為你可以說白馬、黑馬、黃馬都屬于馬這一系統的整體,而如果單說“馬”,則不能代表是白馬。
既然馬不能代表白馬,白馬又為什么會是馬呢?因此,著名的白馬非馬命題也就由此誕生了,而公孫龍當年也憑借這一詭辯的才能,成功牽著白馬走出了城門。
由此可見,名家詭辯的能力想必親們已經略知一二了吧?那么,這樣一個一向注重于詭辯的學派,又是如何出現的呢?其目的究竟為何?
根據漢代學者司馬談的解釋,名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時期的禮官。由于禮官的職責就是掌管文庫典籍,所以這批人在學識上自然要比常人更加淵博,一般人們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在禮官口中得到可靠的答案。
而隨著禮樂制度的逐漸瓦解,禮官早已降至民間,失去了執掌典籍的資格,但腦袋中的智慧和知識卻保留了下來。所以,這一類人后來也就逐漸向為世人解釋一些新興的名詞進行轉變,故而被世人稱之為“名家”。
然而,長時間沉浸于對知識名詞的解釋當中,有一部分人便就此針對“名”和“實”的問題展開了辯論,即我們所熟知的名不副實,以及名實相副。前者著名的論斷正如白馬非馬及堅白論。
(將石頭拿在手中則堅硬,放在遠處則能看見其白色,但白色摸不出,堅硬看不到,所以石頭堅硬和白色的本質,應當區分開來)。
而這種看似充滿了邏輯怪圈的理論,卻是為名家所提倡的偃兵等思想有著密切關聯,所謂偃兵,就是指在名家人士看來,凡事不一定必須由戰爭來解決,軍隊不是解決問題的一切手段,所以名家人士向來都是反對暴力的。
至于說目的,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個學派中的任何一個觀點,都是為了能夠替天下眾生尋找新的出路,名家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這樣一種以詭辯為其主要思想著述的學術流派,為何在戰國末年,就已經逐漸消失了呢?這就和名家的單一性有關。要知道,名家的理論主要來自于邏輯詭辯,并沒有形成新的論點和觀念。
但在諸子百家當中,諸如墨家、縱橫家、法家等學派,同樣也注重于邏輯的推敲。因此,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名家大部分邏輯論述及思想,都被各家及各個學術流派所吸收,以至于最終這一獨立的學術流派自然而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除此之外,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由于我國自古就屬于農業大國,所以任何一種學術流派想要得以傳播,就必須能夠付之于實踐,貨真價實的造福社會和大眾。
但名家的所有學術,都偏向于哲學領域,這就失去了與時俱進的傳承資本。當然了,喜歡抬杠的人肯定又會說,道家也是搞哲學的,為啥人家就能傳承下來呢?
舉個例子,白馬非馬探究的是名實之間的關系,就和公孫龍另一個“離堅白”的學說大相徑庭。簡單來說,離堅白就是指你看到一個白石頭,卻感受不到它的硬度,但你將石頭撿起來,卻只能摸到他的硬度,無法摸到他的顏色。
而你眼中看到的顏色,和手中感受到的硬度,是兩種分開的東西,它們并不能夠被一方同時感受到。這樣一來,白石頭和硬石頭就是兩種東西。
看到沒?說白了,名家探究的話題都很具有哲理性,但卻是沒啥用,最起碼對于廣大勞動人民而言,用處并不大。
但道家不同,道家的哲學與修身養性息息相關,同樣也為人們如何和大自然和諧相處提供了參考和借鑒,自然能夠經久不衰,以至于最終成為中華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名家的沒落只能歸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性。但好在名家的典籍得以流傳,不至于似陰陽家那般被時代的洪流徹底吞沒。
其他文章
熱門文章
-
 打工老板的結局
2023-10-24
打工老板的結局
2023-10-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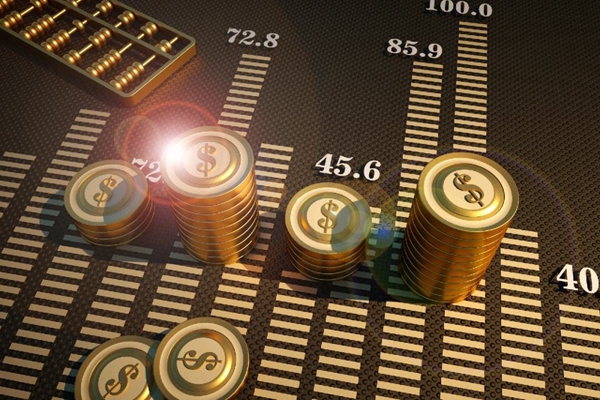 洪漢義12個明星女友名單(14K洪漢義回
2023-09-11
洪漢義12個明星女友名單(14K洪漢義回
2023-09-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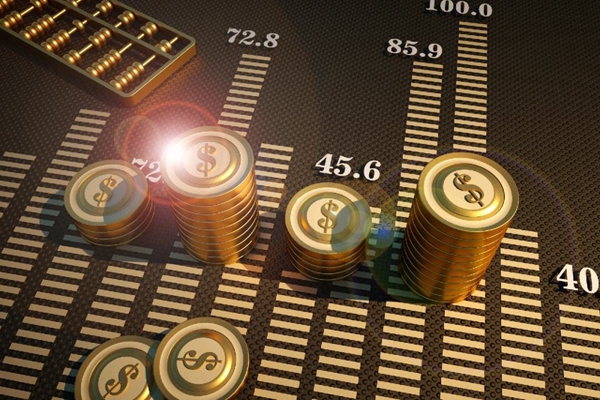 洪漢義12個老婆名單(真正的14k老大女
2023-07-31
洪漢義12個老婆名單(真正的14k老大女
2023-07-31
-
 723甬溫高鐵為什么埋車廂
2023-10-25
723甬溫高鐵為什么埋車廂
2023-10-25
-
 上海70歲以上老人存款規定 上海老年人存
2023-11-19
上海70歲以上老人存款規定 上海老年人存
2023-11-19
-
 瘋癲辦公室人物介紹
2023-10-20
瘋癲辦公室人物介紹
2023-10-20
-
 成功開導老婆接受別的男人案例(男人如何洗
2023-09-03
成功開導老婆接受別的男人案例(男人如何洗
2023-09-03
-
 九一制片廠潘甜甜個人資料(紅人潘甜甜落網
2023-09-17
九一制片廠潘甜甜個人資料(紅人潘甜甜落網
2023-09-17
-
 大耳朵圖圖毀童年牛爺爺和圖圖媽(哪里能看
2023-09-11
大耳朵圖圖毀童年牛爺爺和圖圖媽(哪里能看
2023-09-11
-
 山東最不易發生地震的市
2023-10-18
山東最不易發生地震的市
2023-10-18
